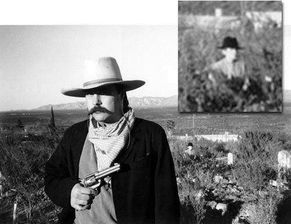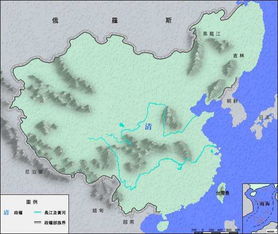钱穆:怎样安顿本身的心?
2022-11-15 13:17:11 作者:眼裏不容劈腿狗我的命運我主宰
教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。——陶行知
怎样安顿本身的心?

文 / 钱穆
一
怎样调养我们的身材,怎样安顿我们的心,这是人生题目中最根本的两大题目。前一题目为人兽所共,后一题目乃人类所独。
禽兽也故意,但他们是心为形役,身是唯一之主,心则略如线人四肢普通官能,只像是一东西,一作用。为要调养身,才运使到心。身的调养临时无题目,心即临时制止其运用。总之,在动物界,只有第一题目,即怎样调养身,更无第二题目,即怎样安顿心。心只安顿在身里,碰到身有题目,心才见作用。心为身有,亦为身役,更无属于心自己之运动与事情,是以也没故意本身独立而自生的题目。
但动物进化到人类便差别了。人类更能运使心,把心的事情格外加重。心的历练多了,心的功效也前进了。心颠末永劫期的历练,心的奉献,遂远异于线人四肢其他身上的统统官能,而缓缓成为主宰统统官能,指挥统统官能的一种特别官能了。人类因能运使心,对付怎样调养身这一题目之解答,也得到庞大的前进。人类对付怎样调养身这一题目,缓缓感得轻松了,并不如禽兽时期那样地榨取。于是心的责任,偶然感触解放,心的作用,偶然感触闲散,这才产生了新题目,即心本身独立而自生的题目。
让我作一浅譬。心本是身的一干仆(注:干仆,指服务醒目的西崽)。因于身时时要使唤它,调遣它,它因于时时运动,而渐渐地增添其敏锐。恰像偶然仆人派它事,它难免要在使命完成之余,本身找寻些欢乐。仆人派它出外活动,它把仆人叮嘱事办好,却本身在外闲逛一番。厥后成了风俗,仆人没事不派它出去,它还是想出去,于是偷偷地出去了,闲逛一番再返来。再厥后,它便把仆人需服务轻快办好,独自一人用心在外逛。是以身生存之外,尚有所谓心生存。
这事并不难相识,只要我们各自反身自问,各自岑寂看别人,我们一天里,时时费心着的本相为什么?怕下一餐没有吃,快会饿去世吗?怕在身之四围,时常有仇人突然来把你杀去世吗?不!肯定不!人类自有了文化生存,自有了政治社会构造,自有了农工商技能生存渐渐不停发明今后,它早已逃离了这些伤害与挂念。我们现在所遭遇的题目,急待办理的题目,十之九早不是关于身生存的题目,而是关于心生存的题目了。
这一题目,成为人类独占的题目。这是人类的文化题目。远从有笔墨纪录的汗青以来,远从有开端的农工商分业,以及社会构造与政治办法以来,这一题目即开始了,并且渐渐的走向其紧张的职位地方。
二
心总爱脱离身向外跑,总是偷闲任意逛,一逛就逛进了所谓神之国。心脱离身,向外闲逛,一逛又逛进了所谓物之邦。科学的抽芽,也就远从人类文化汗青之早期便有了。原来要求身生存之宁静与丰足,时时要役使心,向物打交道。但心与物的谈判履历了相称久,心便也闯进了物的神奇之内圈,发觉了物的种种失常与底细。心的才智,在这里,又碰见了它本身所高兴,得到了它本身之餍足。它掉臂身生存,一意向前跑,跑进物天下,效果对付身生存,也会无益而有害。
五色令人眼花,五音令人耳聋,五味令生齿爽,像老子那一类陈腐的陈言,现在我们不消再说了。但试问科学发明,日新而月异,层出而无穷,何尝是都为着身生存?大范围的生产狂,无穷止的企业狂,专翻新格式的发明狂,实在是心生存在自找出路,自谋怡悦。
若论对付身生存,有些处已是锦上添花,有些处则是多此一举,而有些处竟是自找苦末路。至于像原子弹与氢气弹,那些团体杀人的利器之新发明,本相该咒詈,照旧该歌颂,我们临时留待下一代人类来评判。现在我们所要指述者,乃是人类自有其文化汗青今后的生存,明显和普通动物差别,身生存之外,又有了心生存,而心生存之紧张渐渐在逾越过身生存。现在天的我们,明显已不在怎样调养我们身的题目上,罢了转移到怎样安顿我们的心的题目上,这是本文一个重要的论题。
三
无论怎样,我们的心,总该有个安顿处。
相转达摩祖师东来,中国和尚慧可亲在达摩前,自断一手臂,恳求达摩教他怎样安他本身的心。慧可这一问,却问到了人类自有文化汗青以来真题目之真焦点。至少这一题目,是直到近代大家全部的题目,是大家平常所必定碰见,并且各已深入感触的题目。达摩说:你试拿心来,我当为你安。慧可忽然感触拿不到这心,于是对本身那题目,难免爽然若失了。
实在达摩的解答,有一些诡谲。心虽拿不到,我心之感有不安是真的。禅宗的祖师们,并未曾真实办理了人类这题目。禅宗的祖师们,教人试觅心。以心觅心,正如骑驴寻驴。心便在这里,现在叫你把此心去再觅心,于是证明了他们无心的主见,那是一种欺人的花招。以是禅宗虽曾流行了临时,人类照旧在要求怎样安顿心。
宋代的道学老师们,又教我们心要放在腔子里,那是不错的。但心的腔子是什么呢?我想该便是我们的身。心总想脱离身,往外跑。跑出腔子,飘漂浮荡,会没有个安顿处。何止是没有安顿?没有了身,必定会没故意。但人类的心,早已不肯常为西崽,早已不肯仅供身生存作驱遣。并且身生存实在也是易餍足,易摆设。人类的心,早已为身生存摆设下了一种过得去的生存了。身生存已得餍足,也不再要驱遣心。心闲着无事,那能克制它向外跑。人类为要摆设身生存,早已每每驱遣它向外跑,现在它已向外跑惯了。身常驱遣心,要它向外跑,跑惯了,再也关不住。但是怎样又教民气要放在腔子里?
然而不幸人类之心,又时时真会想游离其腔子,宗教即是其一例,科学也是其一例。宗教可以发泄心的情绪,科学可以睁开心的理智,要叫心不向这两面跑,正如一个孩子已走出了大门,已见过了天下,二心里真生高兴,你要把他再关进大门,使如牢囚般坐定在家中,那非使他发疯,使他烦闷而病而去世,那又何苦呢?但那孩子跑遍了天下,还该记得有个家,有个他的归宿布置处。不然又将会如幽魂般,处处漂浮,无着无落,无亲无靠,依旧会发疯,依旧会烦闷而病而去世的。
中世纪的西方,心跑向天国太远了,太离开了本身的家,在他们的汗青上,才有一段所谓暗中时期的显现。现在若一贯跑进物之邦,跑进物天下,跑得太深太远,再不转头顾到它本身的家,人类汗青又会引致它到达一个科学文明的新暗中时期。这景色快在面前了,稍有远目光的人,也会瞥见那一个黑影已隐隐在眼前。
这是我们当身事,还待细说吗?
让我再归纳综合地一总述。
民气不克不及尽向神,尽向神,不是一好安顿;民气不克不及尽向物,尽向物,也不是个好安顿。民气又不克不及老关闭在身,独裁它,使它只为身生存作东西,作奴役,这将使人类重回到禽兽。如是则我们究将把我们的心怎样地安顿呢?慧可的题目,我们仍还要提起。
此一宇宙,是大道运行之宇宙;此一天下,亦是一大道运行之天下。此同心,则称之曰道心,但实还是仁心。孔子教人把心安顿在道之内,安顿在仁之内。又说:忠恕违道不远,孝弟也者,其为仁之本欤。孔子教人,把心安顿在忠恕与孝弟之道之内。孔子说:择不处仁焉得知?孟子说:仁,民气之安宅也。这不是道心即仁心吗?慧可不明此旨,故要向达摩求放心。宋儒明白其中玄妙,以是说心要放在腔子里。西方文化偏宗教偏科学而此心终不得其所安。以是我在此要专程再提出孔子的教导来,想为民气辅导一布置处,想为天下人类文化再牖启一新前景与新途向。
文章泉源:《人生十论》一书,三联书店 2012年版
图片泉源:网络